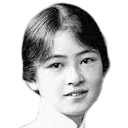島嶼文學
2023-06-07 https://weibo.com/6410774889/N4cP2cbtf
#人選之人造浪者 #臺灣
由台剧《#人選之人——#造浪者》引发的#台灣 #Metoo 从政治圈烧到媒体圈如今烧到了文坛,爆出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性骚扰。
一位是#陈芳明。台湾著名、学者,著有《#台湾新文学史》等。他曾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,包括#林奕含 就读的#政治大学。奕含还拿过自己的《#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邀请他签名。奕含往生后他曾多次发文悼念她。
一位是#郑愁予。以一首《#错误》享誉全球诗坛,诗歌入选两岸教材,作为老牌诗人广为人所知。《#他们在岛屿写作》系列纪录片里的《#如雾起时》主角就是他。受害者在脸书发长文《踩在受害者的位置上,踩好踩满》(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otes/350340429575959 )指控他在2005年担任#东华大学 客座教授期间对学生实施#性骚扰。标题来源于2016年某位#辅仁大学 老师斥责当时站出来发声性侵受害者说「不要乱踩上一个受害者的位置」。
———— ⁂ ————
作家陳芳明遭指為性騷慣犯 政大:將依法調查
2023-06-07 https://news.pts.org.tw/article/640415
#陳芳明 #性骚扰 #Taiwan #metoo #台湾 #米兔
——+——+——+——+——
「我達達的馬蹄」鄭愁予也爆性騷 東華客座期間灌酒女學生還毛手毛腳
2023-06-06 https://www.mirrormedia.mg/story/20230606edi054
#鄭愁予
——+——+——+——+——
政大老師爆「作家陳芳明」是性騷慣犯 要女學生留心一點
2023-06-07 https://www.ettoday.net/news/20230607/2514732.htm
《#家屋》
#林奕含 2017-04-11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otes/%E6%9E%97%E5%A5%95%E5%90%AB/%E5%AE%B6%E5%B1%8B/282277178891518/
外公在我生日前兩天過世了。
外公外婆住台北,最後一次跟外公說話,是十八歲,六年前北上台大醫學的甄試,住外公家。外公的老花眼鏡像滴水掛在鼻頭,金絲結婚戒指埋沒在肉裡。大家一見面就傳授我面試如何如何,而外公只給我講川端康成。現在想起來,外公永遠冰封在那個場景:檜木椅子細而黑的手臂從背後圈抱著外公,日文文庫本偎在他的爛梨色大手裡。
甄試四月放榜,我落榜了,而五月,外公中風了。七月還要指考。外公中風,媽媽整天哭,她不是最小,卻是最受寵的孩子。媽媽朋友談到公婆骨折,她說:對啊,我爸爸中風了。我問她開飯,她說:怎麼吃,我爸爸中風了。跟她上菜市場,魚販子流星般把大魚甩到秤上,魚鱗點點飛濺,魚販子問媽媽:切嗎?媽媽流著淚說:我爸爸中風了。媽媽像被這個句子蠱惑了。我第一次清楚地想到:「 媽媽生病了。」
出加護病房,外公不能說話,也不能進食了,跟進加護病房的隱約不是一個外公。媽媽把外公接到台南照顧,救護車在高速公路上一路啼叫。媽媽在隔壁空地蓋了一間小屋子,我們叫它「小木屋」。小木屋前院種了一棵黃花風鈴木,懶散長枝條的毛孔吹奏出香花,風起的時候,膩亮的綠葉磨蹭撈耙著不肯掉下去,倒是黃花烘烘地一叢追趕著一叢落下去。多少黃花留在樹上,就有多少黃花下到地上。外公外婆一住住了六年,六年,不夠講完一則關於親情之懺傷的大題目,只足以讓一株黃花風鈴木成長、茁壯。
爸媽以為我的作家夢是對考試失利的反動,是在物理化學面前跌跤,所以跟中文私奔。爸媽搞錯了,那就是一次考試而已,要進醫學系,再考個試就好了。我跟海海說不想生小孩,說我外婆身體不好,媽媽身體不好,我也不好,怕小孩也不好。海海說:妳身體不好是後天吧。但我想說的其實是:我怕我生出一個憂傷的小孩。
第一次大學休學之後,踏上自我毀傷的旅程。
媽媽生病的主要症狀是裝潢,或用哥哥的話是:把房子打掉。醫學上簡易判斷病態憂傷或正常憂傷的方法是:是否搬動親人的物品。常看到好萊塢拍一個小兒子的房間,一切都跟兒子死去那天一樣,筆記本露出整齊齒牙,鋼筆禮貌地脫了帽,陽光大把灑進來──這就是病態憂傷。但媽媽的病態憂傷是反其道而行的。
我有段時間住在台北外公家。媽媽上台北,沒辦法絲毫忍耐待在外公健康地存在過的這空間,於是把裝潢都打掉。油漆搔出皮屑,木地板被挖禿,露出鼠色的水泥和不停吞嚥的管線,櫥櫃被連根拔起,只木疙瘩、木樁木刺留在那裡,大有焚林之勢。施工期間,晚上我睡厚紙板,鋪在泥沙上,在房間中央,像個島。睡在一桶桶混凝土之間的機會比睡在野外還少。反正我無論如何睡不著。
有天媽媽打電話給我,她要重新裝潢台南我房間,也就是打掉。我心想:大概不祥吧。設計師問媽媽,壁燈上那一圈窗簾繩是在幹嘛?媽媽對我說,她立刻看出來了,那是,在幹嘛。她說奇怪她走進那房間從來沒看見。我心想:媽,對不起,但這不是我的錯。一個人接觸過死亡又拗回去,那敗壞的氣息很難不透露出來。死是種體味。同樣的,一個房間的主人在裡頭尋死,沒辦法保證房間不向參觀者洩漏它的祕密。
我記得自己融化在床上,我的眼睛在我的肉塊上各自仰泳,看著爸爸媽媽罵我的髒話,髒話呈標楷字,鬼魂一般灰階斜體地在房間蜉蝣。在那樣一個房間,除了死,妳真的沒有其它事好做。糯米色的絨布窗簾繩子,兩個結成一圈,掛到水晶壁燈上,腳下的椅子爬滿了鏤花藤。多麼富麗,而一切太明顯的對襯修辭都是可惡的。物質當然可愛,但前提是精神也可愛。原來被物化的愛情才真正難以挽回。噩夢醒來,也只是剝開一個噩夢,被窩藏在另一個噩夢裡。
是,我的家人會很傷心,是,這不能解決問題。那誰來解決我的傷心呢?楚楚醫師說:門診每天都有自殺的病人,我們只會「邀請」那些並非以死威脅,並非以死求重視的病友「入住」我們的病房,簡言之,就是「真的想死」的人。
我常常想起加護病房不熄燈,無所謂日夜,一小時抽一次動脈血,動脈針好粗,針筒歡喜地充血,而我很乖,很溫馴。紅的、黑的、透明的管線鑽出我的身體,望上爬到各種機器上,一嘔吐,心電圖就會尖叫,我彈起上半身,牽扯那些管子,像風中樹。也常常想起精神病房,鐵欄杆的影子像棍棒。窗外棕櫚的羽狀大葉子像隨時可以飛走,風景被欄杆切成垂直一片一片,像小時候躲貓貓,躲在衣櫥裡,視野乖巧地被百頁割成水平一片一片。
外公家前面的公寓管理員老看我。他不超過三十歲,每踏進巷子,就感覺到他把眼球軟搭搭投擲到我臉上,我一路沾黏著那雙眼球。總不能叫他停,顯得自以為是。
有個秋夜,我爬出陽台的鐵欄杆,站在陽台之外。高風把裙裾上的玫瑰吹胖、吹活。手抓著欄杆,腳踩在柵字式欄杆的那一橫劃上,連腳底板也嘗得到鐵鏽的血腥味道。我想:「只要鬆手,或是腳滑,後者不比前者更蠢。」人車沒有想像中小,也沒有想像中少;奇怪,痛苦的時候,可以訴說的人都睡深了,這時人聲卻蒸騰著飄上七樓,像意義上的二手菸。還活著的人都是喜歡活著的人嗎?我非常非常傷心,因為我就要死了。此時,望下看見管理員又在看我,折斷似把頭磕在後頸,眼神清潔,彷彿他抬頭看的是雨或是雲,腳釘在馬路上,也沒有報警或喊叫的意思。當下只有一個感覺:這太丟臉了。爬回陽台,俐落得不像自己的手腳。
回想起來,我幾乎可以肯定那會是我人生中最羞恥的一幕。因為甚至討厭,所以這拯救無所謂匹配,如此留情。羞恥最大的成份正是生命力,並不是生命的特徵是羞恥心。
外公是一個非常日式的人,無論去哪裡總要穿西裝繫皮帶,西裝褲筆直,唯一崎嶇的地方是口袋裡的文庫本。外公喜歡上咖啡廳,我還只喝奶茶就帶我上咖啡廳,他呷一口咖啡,吃拉麵樣發出窸窣的聲音,說:「好,這個好」。我總說,唉額,好苦。咖啡在我的牙齒留下痕跡,但是會放過外公,因為是假牙。外公還喜歡給我做鮪魚拌芒果,好像我從沒換過牙。也無從知道我成年之後外公還會不會給我做鮪魚拌芒果了。
外公住在小木屋六年,回台南我喜歡找他說話,學電視唱歌跳舞,儘管不確定他是否聽懂,也不確定他是否認得我。外婆喜歡說,外公以前最討厭人家叫他講國語──外婆模仿外公:「什麼國語?是北京語!」外婆笑著笑著,笑出眼淚,遂哭起來了。
六年之間,外公進出急診無數次,或肺積水,或肺水腫,都一樣,反正我都聽不懂,我只知道,不是這次,就是下次,或是再下一次。都一樣。跟在救護車後面,直駛進大學醫院,每次都發出病危通知──第一次發通知,來了很多人,很多眼淚,長一輩的,我輩的。再發,就少些人。發到最後,只剩下外婆和爸爸媽媽。
外公在棺木裡看起來好小好小,又變得更小,小到被塞進一個罈子裡。骨頭白得像外公自己。外公,對不起,我不是一個好孫女,我讓你最喜歡的女兒那麼難過。
死亡,所謂死亡之路,不是電影裡那樣,晴雲樣的白枕頭,白床單,床頭香水瓶似的藥罐,說完一句優雅而智慧的話,一隻手撲通掉出被單外。真正的死亡之路,一張病危通知引領你走向下一張,一路消毒水如雨,灌溉出五顏六色的藥丸,一顆藥丸落下地,抽長出更多、更繽紛的藥丸,很多吐物、膿血、屎尿,太多的眼淚。旁人再怎麼愛也不能幫你吐酸水、痾硬屎,旁人只掉眼淚。從家裡到醫院,醫院回家裡,幾十對往復折線,把這折線小心翼翼地拉開,像拉一架手風琴,這才是死亡的漫漫長路。恰恰跟我走回生命的路一樣。
2015.03.16
——+——+——+——+——
林奕含:
前年生日的舊文,現在看來一點點幼稚了,但是沒想改。也歡迎轉貼喔。
寫房思琪跳樓那段,我是整個用這散文挪上去的
我想,寫小說,挪用自己的經驗,這在所多有
馬路的溫度、樹影、膚觸...只是我挪用的例子極端點而已
讀了許多心得,說看了小說難受痛苦,失眠噩夢
啊我真是用命下去寫的呢
“我现在读小说,如果读到赏善罚恶的好结局,我就会哭,我宁愿大家承认人间有一些痛苦是不能和解的,我最讨厌人说经过痛苦才成为更好的人,我好希望大家承认有些痛苦是毁灭性的。”
#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#林奕含 #性別平等 #女性主义
(by: NGOCN)